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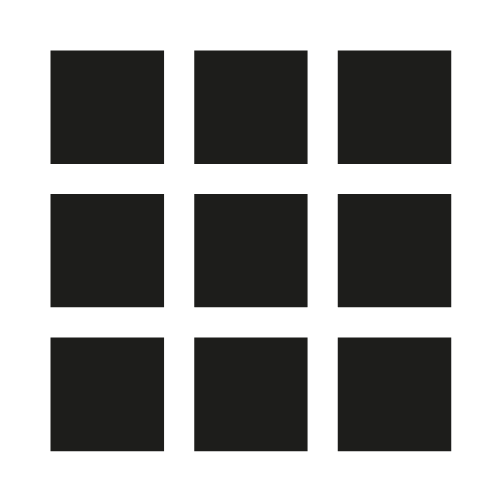
社群參與的公共藝術項目,在強調公眾參與度時,可能只著眼於公眾的參與人數,止於有沒有讓社群「開心」地參與,卻少有探討參與經驗有沒有提升社群對社區,以及藝術的理解,及參與者自身的創作能量有沒有因此被釋放。又或,有沒有回到文化藝術的角度去進行研究及論述,以至探索社區藝術項目的各種策略與理想等。
計劃邀請了三位評論人:張薇、阿三及黃嘉瀛,擔任今次計劃的「觀察員」。他們將會分別出席計劃的不同活動,了解藝術家設計藝術經驗的理念、構思,又或會與藝術家及參與的社群、公眾交流,了解他/她們的體會,透過觀察員的視點,將會為社區藝術項目打開另一層次的閱讀及思考。
To see how well the public engaged in a certain community art project, it seems out of focus to check whether the people “enjoyed” the project or not. It’s even more distorted to determine only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Did the experience rai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as well as arts? Did the people’s creative power unleash? Going back to the angle of art and cultural analysis, did the project study, comment or even explore various strategies and ideals of community arts?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This project invited three critics, Cheung Mei, Chan Sai-lok and Ky Wong, to be the “observers”. They will attend various activities and learn how the artists designed the art experience. They would even communicate with some participants and the public to find out how they perceive. The observers’ unique views will unfold a whole new level of understanding about community arts.
觀察紀錄目錄
張薇 Cheung Mei
張薇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和美國紐約大學跨學科人文思潮碩士課程,從事文化藝術的報道及編輯工作多年。1999年獲亞洲文化協會利希慎獎助金。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
Cheung Mei graduated from Journalist and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John W. Draper Interdisciplinary Master’s Program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University. She has worked as an arts and culture journalist for many years and received Lee Hysan Foundation Fellowship from Asian Cultural Council in 1999. She is now a freelance writer.
陳世樂(阿三)Chan Sai-lok
藝術家、藝評及寫作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後修畢藝術碩士(創作)及性別研究文學碩士課程。近年展覽包括「The Name Red」(2021)、「Everyday Practice」(香港及紐約,2019及2020)及「一夕餘地」(2019)等。曾入選Sovereign傑出亞洲藝術獎及獲大華銀行年度水墨藝術大獎等。現為藝評組織Art Appraisal Club創會成員、網上藝評計劃「時刻導賞員」總監,及電台藝術節目嘉賓主持。
Artist, art critic, and writer based in Hong Kong. Chan holds a BA and MFA in Fine Art and an MA in Gender Studies, all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recent solo exhibitions include The Name Red (2021), Everyday Practice (Hong Kong 2019 and New York 2020), and Land of Longing and Exile (2019). Chan has been a finalist in the Sovereign Asian Art Prize, and a winner of the UOB Art in Ink Award. Chan is a co-founder of an art-critic-collective Art Appraisal Club, project director of an art review project “Free Walk In”, and guest host of a radio art program.
黃嘉瀛 Wong Ka-ying (KY)
黃嘉瀛,香港藝術家,於2013年獲香港中文大學藝術學士及於2021年獲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哲學碩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生。策展項目、藝術創作及寫作散見於香港及其他城市之報刊、美術館及社區空間。
www.wongkaying.com
Wong Ka-ying (b. 1990) is an artist and writer based in Hong Kong. She received her BFA degree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13 and obtained her M.Phil. Visual Arts fro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 2021. A keen observer of the art community and society, Wong critically reflects on the various social, cultural, and gender issues today through using a wide range of media from performance to social media platform. Wong expresses passion in writing, curating and art educations. She made an outward appearance on various public sharing, seminars, panel discussion and talks, actively engaging with the communities and art lovers.
觀察紀錄 #1-1
大家的掃把 大家的公園
張薇 (計劃之觀察員)
有一套多啦A夢大電影叫《日本誕生》,講述大雄離家出走,卻發覺現代社會無論是閒置空地還是公園,全部都已被「擁用」,於是決心回到史前尋找尚未屬於任何人的空間……
香港的公園雖說是為公眾而設,但規例密密麻麻幾頁紙,羅列出規劃者想得出的「不得」做之事。但規劃者規劃不到公眾「可以」做的事——即使設計了棋盤也控制不了下棋的方式。公園的使用者透過日常生活的運用,形成公園「可使用」的規則——非正式、不明文、協商、約定俗成、浮動,甚至有時是雙重標準的。很多使用方式看似隨意、細微,但卻有著難以阻擋的韌性。程展緯的灣仔公園快閃掃樹葉活動本來安排在星期天舉行,也因未預先考慮外傭放假會在公園聚集而需臨急改期。大批外傭的空間需要就是這項空間使用最強大的正當性。
第一次快閃時吸引了一位平時來觀棋的伯伯,退休前從商的他認為這麼多年輕人來掃地「不符合成本效益」,亦表示掃樹葉揚起塵土會影響遊人。我想正是這十個參加者十把掃把在這個空間所形成的陌生景觀,讓人看到了每天都在這裡打掃的清潔者以及工具背後被忽視的勞力;他們的服務讓公園成為「大家的公園」。
或者大雄不過早放棄,先來為他的社區掃落葉,就不用回到冰河時期去擁有一片屬於他的空間。

觀察紀錄 #1-2
大樹是時空隧道
張薇 (計劃之觀察員)
程展緯先是看到地上跟在清潔工掃把後面跑的小樹葉,繼而看到半空中繼續無情地飄在清潔工身後的落葉,再看到落葉所屬的大樹身上掛著的名牌。
灣仔公園其中一角的落葉,主要來自兩棵有著龐大樹冠的老樹——樹頭菜(魚木)和細葉榕。樹頭菜是落葉喬木,除了落葉,它的花期也會製造壯觀的花瓣雨。細葉榕是常綠喬木,除了全年都有樹葉更替,果期更會掉落一地紫色榕果。這兩棵樹都是列入了政府古樹名木冊的古樹,程展緯好奇地想,若將名冊中百年老樹的所在「點」連起來,是否正好呼應著香港島的天然海岸線。有趣的是,在灣仔區(維園除外)這個想法的確頗接近現實。
正如毒蛇出沒的地方必會生長著能解蛇毒的植物,程展緯在這兩棵大樹旁邊,發現了蒲葵樹,它的枯葉做出來的掃把,最適合用來打掃落葉。蒲葵樹,是棕櫚科不分枝喬木,可高達十多二十米,除了是香港巿區常見的綠化樹木,亦具生態價值,葉下棲息著香港巿區常見蝙蝠短吻果蝠。它也是大葵扇和簑衣的材料,在民間傳統文化中佔有席位。
如果住在灣仔公園附近的居民,能用灣仔公園的蒲葵葉製作掃把,打掃灣仔公園百年如一日地飄下的落葉,是多麼有詩意的行為。程展緯就用「大家的掃把」工作坊和之後的快閃掃樹葉活動,將這個行為實踐出來。
工作坊後,參加者每人手握一把親手製作的掃把,從灣仔集成中心沿著灣仔道進入灣仔公園。在這短短一段路程,他們經驗了由灣仔的填海區沿著原有的天然海岸線轉入已消失的摩利臣山。150年前這座山丘因開採石礦而被移平了,相信也是在那之後不久,這兩棵古樹就種了在這裡,自此以後成為比周遭任何景物更久遠的風景。
今天的落葉,掃著飄了一百年的落葉,讓人有某種幸福感。這會否就是一個人生活在一個社區希望獲得的連繫與接納?

觀察紀錄 #1-3
喚回工作的樂趣
張薇 (計劃之觀察員)
在「大家的掃把」,程展緯希望大家關顧社區中的勞動者,與他們產生聯繫。其中一個活動,就是舉辦工作坊,運用由不同清潔工的經驗與智慧總結而來的方法,和街坊一起親手製作一把用來打掃落葉的蒲葵葉掃把,透過改良工具來免除不必要的辛勞。
在掃把工作坊可感受到參加者的投入和愉悅。從大自然擷取物料、靈巧地運用雙手去製作自己的工具,在現代社會已是陌生而遙遠的體驗。在另一個「大家的坐墊」工作坊,亦可在參加者身上看到同樣的專注。程展緯在公園認識在那裡工作的芬姐,她利用廢棄的包裝膠條為員工休息室編織坐墊,每一件編織品都讓人感受到編織者和使用者的體溫,看到辛勞工作後休息的人。
日本民間藝術理論家柳宗悅認為,手工藝作業是最適合人類的工作,因為手與心相連,在使用手「踏實而仔細」地製造的過程中,「自由和責任得到保障,因為這樣的工作伴隨著快樂,同時還顯現出新產品的創造力。」當人類被機器指揮,「工人的種種樂趣被剝奪了」。
這幾個與手藝相關的工作坊提醒了我們,工作本來是包含樂趣的。當我們將工作時所需要的創造力釋放出來,就可以讓工作少一點機械,多一點人性,樂趣才可以出現。也許對現代勞動者來說,要獲取工作中的樂趣比起勞力的輕省更奢侈;比起對他們在勞力上的付出,奪走他們在工作發揮創造力的空間,是對他們更大的剝削。而殘酷的現實是,有的清潔工連選擇掃把的自由也沒有。

觀察紀錄 #1-4
先有「大家的」,才有「公共」
張薇 (計劃之觀察員)
大家的籃球
程展緯幾年前曾在籃球場上放過「公共籃球」、「大家的泵」 。相信當初他選用「公共」或「大家的……」這名字時,並沒有在遣字用詞上講究。但我覺得兩者有著根本的區別。觀乎這兩個行為所帶出的意義,我覺得用「大家的」來描述更為貼切。
成語中有「化整為零」和相反的「化零為整」。當中「整」是整體,「零」卻不是什麼也沒有的「零」,而是「一」,「單一」的「一」、「孤零零」的「零」。「公共」(public),是「化零為整」,無數個體融入了整體而呈現出一個總體面貌。「大家」(everyone)卻是「化整為零」,指向某特定群體中的個體,讓人看到自己。舉例,如果說村莊裡的果樹是「公共的」,那麼你行過摘它的果實來吃就會作賊心虛;如果換成說是「大家的」,就人人可摘而不用有所顧忌了。
將一個籃球放進一個社區球場,預計了有一天它會不見了,被某一個人拿走,變成自己的。但每一次經過球場,看到那個籃球還繼續被使用,這情景會給予人力量,令人覺得鼓舞,因為使用過籃球的人透過將籃球留下來也參與了這件事,使籃球真正成為「大家的籃球」。
大家的掃把
在康文署和灣仔區議會合辦的《見山不是山》跨領域藝術計劃裡,程展緯的項目叫做「大家的掃把」,這次他希望在灣仔區的公園內放置一把「大家的掃把」,讓住在附近的街坊隨時可以拿來打掃公園的落葉。如果放下一個「大家的籃球」是以送出一項禮物的形式來表達對社區的歸屬感,那麼放下一把「大家的掃把」,是製造一個履行義務的機會,為大家對社區的歸屬感找一個表達方法。
首先,這把掃把必須經過大家一起製作來成為「大家的」,包括製作掃把的方法、物料,也都是來自大家的。
程展緯曾經當過掃街清潔工,並由此開始留意清潔工的工作細節,知道掃石屎還是掃泥地,掃樹葉還是掃煙頭,晴天掃還是雨天掃,用不同的工具效率大大不同;他亦了解到不少清潔工都會運用經驗加上智慧,自製最合用的打掃工具、遮風擋雨的服飾,甚或運載工具的車仔。
他在大埔就遇到過一個清潔工會自製掃把,每遇到蒲葵樹的落葉,必會存放起來。利用殘舊竹掃把的骨架,紮上蒲葵樹的大塊落葉,就自製出新的掃把。負責的範圍大、要打掃不同表面的清潔工,他們的工具車上必定備有不同用途的掃把。
程展緯先對製作掃把的物料,做了一些資料蒐集。除了最常用的竹枝,華南地區的農村地方都會用分枝多且堅靱的常見灌木——崗松;在一間賣菲律賓貨的舖頭,可以買到至少兩種掃把物料,一種材料不詳,一種是椰子葉的葉骨。後者更是以原材料的形式從菲律賓入口,相信香港肯定有人已擁有使用這物料的手藝;在另一間雜貨舖,他又找到另一種物料,是由高梁桿紮成的掃把,技條還帶著高梁的種子;又有一次,當他在灣仔公園遊走時,手上的高梁掃把吸引了一個少數族裔街坊的注意,雖然有語言隔閡,但她還是主動分享了家鄉的傳統做法。
實地測試過不同物料的掃把後,他發覺若用來打掃公園落葉的話,蒲葵葉掃把是最佳工具。蒲葵葉的尾擺長而柔軟,能接觸較大面積,且易於形成適當的弧度來緊貼地面,使掃把覆蓋範圍內的樹葉不易漏走,再加上每一下掃地動作都會產生一陣微風,帶動著樹葉一起向相同方向跑,在晴天硬地上使用起來,效果比起硬身的竹掃把好得多。
用大埔清潔工送贈的蒲葵葉,程展緯試造了數把蒲葉掃把,並拿到灣仔不同的公園,請清潔工試用,收集意見,交流心得。改良後的成品獲得他們認同為掃樹葉最好的掃把。期間,他每當坐巴士穿越巿區,亦會四圍張望。他發現蒲葵樹不獨是港九新界到處可見的行道樹,不少巿區公園也都有種植。如果收集它的枯葉來製作掃把,不獨不需花費金錢,還能將廢物升級再造、賦予新生,減少堆填區的負荷,既符合政府推廣的減廢理念,也是社會認同的價值。
蒲葵樹,英文名Chinese Fan Tree,顧名思義,它最令人熟悉的用途,就是製造舊時最常用的納涼工具——大葵扇(因為大衿姐愛用,使它在締結姻緣上也有一席位)。把蒲葵葉曬乾,剪成圓形,再用布料收邊就是一把輕便的大葵扇。蒲葵葉又常被用作簑衣,在去年夏天的某一天,程展緯在林錦公路碰見蹲在路邊花槽上除草的園藝工人,她們就是披著蒲葵葉簑衣,以遮擋突如其來的大驟雨。工人慷慨分享了簡單的穿戴方法,還贈他一塊蒲葵葉。
如此常見且承傳著眾多常民智慧與集體記憶的物料,放在一個社區活動中使用是最好的選擇。
程展緯找到擁有一棵樹齡140歲落葉喬木——魚木的灣仔公園,作為一個主要試點,希望運用公園蒲葵樹的落葉作物料,邀請灣仔街坊來製作掃把,再把掃把放在公園內,成為「大家的掃把」,讓街坊都能為自己社區的公園打掃樹葉。
大家的公園
「師兄!」「師姐!」做過清潔工的程展緯使他與公園清潔工同聲同氣。清潔工身份讓他以相同視角來關注他們的需要。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工具,巿區公園的清潔工多數都只能使用公司提供的掃把,但他們都對怎樣的掃把適合處理怎樣的環境、用什麼樣的力度和手勢能使工作事半功倍等,有很多長時間累積而來的觀察和建議。收集意見後,他把自己做的掃把,逐一拿給他們試用,一齊研究改良的方法……
同時,他又自行印製了一件制服,方便「穿」上另一身份——「灣仔公園駐場藝術家」。收集公園的落葉來造掃把的想法,看似簡單,卻因牽涉不同職權範疇,而無從入手。例如,清潔工負責打掃地面的落葉,還掛在樹上的枯葉則屬園藝工人管理的籌疇;而園藝工人修剪下來的枯葉,只能成為公園垃圾被送去堆填區;公園棄掉的廢物不能取,在公園放下一把大家的掃把卻又觸碰其他管理條例……他希望藝術家這個身份能為不同範疇建立一些連結。
對程展緯來說,「大家的掃把」的意義,就是透過這個過程,讓同屬康文署轄下的公園管理部門和文化節目部門兩個平常工作互不重疊的團隊嘗試進行溝通,發現各種未打開的關係網,連結起街坊,為他們找到關注社區的入口。
改變未必能在短期發生,但透過製作掃把集合了大家的智慧;透過工作坊和快閃掃葉活動,一班街坊有了大家的社區介入經驗,成為日後繼續參與的「研究團隊」潛在成員;得到另一個公園的清潔工支持,活動期間收集到一批蒲葵葉,因為沒有存放空間,為了不送去堆填區,程展緯呼籲街坊前來製作大葵扇,送上「大家的風」;因為經常在公園遊走,他還結識了另一公園員工、編織高手芬姐,邀請她首次分享技術,教大家用重用的包裝塑膠帶,編織出「大家的坐墊」,為社區椅子添一點溫柔體貼……
這些都是由「大家的掃把」連結而來的「大家」的故事,在「大家的掃把」真正能放置到公園之前,就是這些點點滴滴的參與,為一個空間填上個人的記號。一個公園又好,一個地方又好,在擁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之前,希望大家每人一小步,首先令它成為「大家的」。

觀察紀錄 #2-1
解心啫,做乜又叫起粵謳嚟?
阿三(計劃觀察員)
音樂人許敖山在五年前一項文學活動上,認識到粵謳這種民間唱頌形式。他在「見山不是山」計劃中成立「解心樂團」,希望跟一眾參與者,古老當時興,過去現在鳴,在街頭一起「解心事」。
「粵謳」是甚麼?粵謳類近南音,是以方言寫成的廣東民間詩歌。不過,它比南音早一點,繆蓮仙〈客途秋恨〉其實是承粵謳風潮而寫成的經典。
相傳,讀書人招子庸在廣州珠江跟一名妓女秋喜暗生情愫,相知相羨並欲白頭偕老。然而,他得上京會試,離開前許下承諾,試後回來迎娶。惜秋喜債主臨門,無法償還款項,她在追逼下跳入珠江,不幸溺斃。招子庸回來知悉事件,傷心悲痛,作〈吊秋喜〉 以解相思之苦。 道光八年(1828年),曾任山東青州府知府的招子庸出版《粵謳》(廣州西關澄天閣出版),合計一百二十餘首。
粵謳偏向詩體裁的興體(即抒情體),以廣東方言入詩,章法極為自由流動,平仄用韻並不嚴格,且常用感嘆詞。「唉」、「咯」或「呀」加強了語氣與情感,或更貼近生活情狀。當時的粵謳多描述妓女的幽情及可憐身世,說唱時以木魚及琵琶和奏,抒發無盡的同情與關懷。這種雅俗共賞的民間詩歌,深受歡迎,吸引不少文人雅士仿效創作,後來甚至被譯成英文《Cantonese Love Songs》。《粵謳》一書流行,第一篇〈解心事〉幾近等同粵謳,故粵謳又俗稱「解心」。
不過,「解心樂團灣仔遊」合唱的,是「珠海夢餘生」廖恩燾撰寫的《新粵謳解心》。欲知來龍去脈,有待下回分解。
/////////////////////\\//
參考資料:
許地山〈粵謳在文學上底(的)地位〉,載於陳平原編:《許地山散文全編》(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289至292。
Morris, P.T, Cantonese Love Song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iu Ji-yung's Cantonese songs of the early 19th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觀察紀錄 #2-2
外交官員寫「新粵謳」以解心?
阿三(計劃觀察員)
上回講到,招子庸以廣東方言創作粵謳(1828年出版)文學民歌,廣受民眾歡迎,成為潮流。差不多一百年後,清朝告終,民國成立,中外有識之士紛紛提倡白話文運動,改革社會。生於顯赫家族的外交官廖恩燾(1863-1954,註一)深明當時情況,「認為推廣文化,普及教育,必須從方言入手,文從字順,同聲同氣,加以韻律成誦,更能聲入心通。」(註二)同時,他深受粵謳打動,認為「粵謳蓋天下之至 文妙音也 其言甚淺而意甚深」,「吾粵語言特異 其歌詞音調不與中原相接」,這種藝術形式有股扣人心弦的魅力,「能使吾心似悲似喜 似迷惘似覺悟 惝恍焉不能自主」。(註三)
據說,年近六十歲的廖恩燾,於1921年到日本養病。至1923年期間,他仿照招子庸《粵謳》形式,創作《新粵謳解心》,後於1924年以「珠海夢餘生」名字出版。
既然說得上是「新粵謳」,題材除了風月私情外,更借歡場百態評論中外時事,又關心國家人民,揭盡社會光怪陸離現象。這創作取態,上承「詩言志」的文學傳統,借風月談人生哲理、做人處事與生活經驗。寫作風格上,使用白話又用詞典雅,引經據典翻出新義,保留粵語入詩的妙趣,意味極為譏諷,字面詼諧惹笑。
《新粵謳解心》共一百零四篇,如〈人唔係易做〉、〈鴉片煙〉、〈咪話唔信命〉、〈咪話唔信鏡〉及〈勸你留番啖氣〉。許敖山的「解心樂團灣仔遊」所唱的,就是首篇〈解心〉。〈解心〉一曲如粵謳曲風序言,談到對住珠江明月,撥起琵琶線,彈出句句真情。借粵謳唱出「雛鶯同乳燕」心中的「無限離愁別恨」。倘若解得開,「條心就軟咯 重快活過神仙」。一眾參加者學習〈解心〉,並及到街頭試唱時,有否心神意會一百年前的民間機智與哀愁?
註一:廖恩燾,字鳳舒。廣東惠陽人,清同治二年生,為廖仲凱之胞兄。九歲赴美就學,十七歲回國。 光緒十三年(1887)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先後出任多國使館代辦及總領使等職。從事外交工作凡五十年之久,著有《嬉笑集》及《新粵謳解心》二書,退休後居香港。
註二:梁羽生:〈重印《新粵謳解心》前言〉,載於廖鳳舒著《新粵謳解心》(重印本。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頁11。
註三:廖鳳舒:〈新粵謳題後〉,同上註,頁223。
////////////////////\\//
參考書籍:
廖恩燾著:《新粵謳解心》。香港:出版社不詳,出版年份不詳。(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小思老師捐贈。)
廖鳳舒著:《新粵謳解心》。重印本。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

觀察紀錄 #2-3
廟街風情以外的社區想像
阿三(計劃觀察員)
上兩回講到粵謳的歷史身世,或者大家心中有一個疑問,粵謳和社區有甚麼關係?
音樂人許敖山(Steve)直言:「其實兩者沒有甚麼關係。」他一心想跟參加者在街頭唱歌,而粵謳的廣東話說唱形式吸引了他。話雖如此,香港人都知道甚麼是廟街賣唱,或看過經典電影《新不了情》,袁靚靚飾演的角色癌症復發,馮寶寶重踏街頭唱出電影最後一曲……稍等!今次「解心合唱團」不是這種想像。
社區演繹地道語言文化。粵謳「無譜」,章法隨性,自由開放。Steve重新編唱粵謳,是根據中文一字一音的特性、廣東話說話的節奏及語氣,及「解心事」內容意思。說唱,強調每個人對歌詞的理解及想像,再用自己的聲音及語氣演繹。粵語有九種聲調,同一字偏少少音、改動一下語氣、斷句位置或節奏,整個意思就不同了。再加上感嘆詞應用,粵謳唱出來的感覺,跟地方、族群和區域文化關係密切。
社區讓人們平等地連結起來。粵謳本為獨唱曲目,「解心樂團灣仔遊」則似合唱團般在街頭「報佳音」。樂團公開招募,來者不拒,參加者是否住在灣仔,或跟灣仔有沒有關係並不重要。報名者不論年齡、性別、階層、國籍、文化及教育背景,或曾否參與音樂表演,都歡迎加入。
我們跟陌生人,基於不同原因、情境或機遇而認識,甚至共同達成某些事情。解心樂團不介意唱得好或不好,排練不必至圓熟無瑕;所有人在同一旋律上,可各自發揮。一起參與,互相信任,彼此尊重,生活本該如此,具生命力的社區更該如此。接受未知,容讓可能,人人平等,大家好像集體玩「糖黐豆」遊戲一樣,有時聚合,有時彈開。曾參與修頓球場拍攝的參加者說自己算是灣仔街坊,但一直沒機會跟球場裡的叔叔交流;今次演出,終於有機會跟他們做了幾分鐘的朋友。

觀察紀錄 #2-4
香港人有甚麼心事未解?
阿三(計劃觀察員)
終於講到最後一回。不知道大家對社區與人和地道方言有甚麼看法。今次想換一個角度,去理解粵謳和社區。
社區是發聲的場所。舞台演出與街頭合唱是兩碼子的事。音樂人許敖山(Steve)有街頭演出經驗,所以排練的其中一個重點是要參加者開聲。聲開了,才可以發;發得響亮,人們才聽得見。那不是說「鬥大聲」,而是將粵謳融入車水馬龍的灣仔鬧巿。位於灣仔中心的修頓球場、「打小人」聞名的鵝頸橋,及建築別豎一格的合和中心,自然成為合唱團選擇地方。那些地點是不少灣仔人的記憶,甚至是香港城市印象。
至於莊士敦道及軒尼詩道交界、茂蘿街7號門前,及黃泥涌道通往馬會的隧道,又為何成為拍攝地點?茂蘿街一帶,是舊唐樓商住橫街,保留了老灣仔的生活風貌;黃泥涌道行人隧道,聲音迴盪效果像個室內表演場地。莊士敦道及軒尼詩道交界是電車拐彎處,人們過馬路的停留位置。途人如水流動,合唱團在島駐足;電車慢駛貼近,車上乘客彷如坐上包廂,當了半刻的觀眾。解心樂團不其然嵌入灣仔的中心。城市環境聲與說唱聲,粵謳舊年代的詞與現代人的口音,隱若地成為城市聲景的一部份。
社區也是個動詞,讓我們可以在街頭自由活動。街道由人們設計,把空間劃分成不同功能。車該往哪裡去,人要沿哪邊走,店舖、公共設施及私人地方區別得清清楚楚。城市規劃概念建構了我們行街的經驗。因為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興建邏輯,不同地方有不同文化面貌,所以各城市有各自的行街特色。
行街,應該跟購物沒有必然關係。上班途經的奔波,放學閒逛的青春;周末跟死黨去踢波,情侶一雙一對去睇戲;到298商場砌電腦,進政府大樓申請證件;探一探許久不見的親友,或跟即將移民的老友話別餞行。除了行街,我們在路上還可以做些甚麼?依稀記得,人們可曾在街上休息、聊天、發呆、吃飯、午睡、做功課、追逐、玩耍、乘涼、抽煙、打麻雀、晾衫、曬被,或風乾海味藥材。其實,我們還可以在街上自由自在地歌唱。街道從來屬於我們。因為我們能夠隨心所為,我們才會記得灣仔,認同灣仔跟我們有關。而社區,才會成形。
如果有一天,街只可以行,或者容不下駐足,我們就得想想這個城市發生了甚麼事。粵謳盡是遺憾與感慨,未知Steve有否察覺粵謳可以是我城的隱喻。計劃在疫症爆發之下總算結束了,參加者其實耳猶未盡,而香港人可有甚麼心事未解?
「心事千遍都解佢唔開……但終須會有一遍,解得開。」
有緣再會!各位保重。

觀察紀錄 #3
連鎖對話
黃嘉瀛(計劃觀察員)
1. 前奏展覽
「夏天」這季節置於香港似乎份外悶熱。甫踏進商住大廈混集的灣仔,困在樓與樓之間的熱氣撲面,老土也要說句真是車水馬龍。許多在灣仔的商業大廈中工作的打工仔,夏日一放午飯就會從冷氣辦公室大批遷移到冷氣商場避暑,集成中心就是其中一處集中地,偏偏在這商場地下,保有一角特別安寧。我在2021年7月踏進《見山不是山》前奏展覽時,就有這種感覺。
這展覽展示了計劃中的藝術家未來創作計劃的簡單介紹,同時招募公眾參與活動。看過計劃簡介後我馬上就被旁邊牆上的雙頻錄像裝置吸引駐足。那是兩段藝術家循不同路線遊走灣仔的「拍攝者視覺」錄像,錄像鮮有人物入境,多是街道風景,有時停頓,有時踱步。視像前的長椅上有耳機,原來耳機播放著藝術家拍片時同時收錄的環境聲音、喃喃自話以及一些隨意的對話。散步作為獨處和面對自我的一種方法,這作品看得人特別舒心。
牆上的架子放著一本白色記事簿。來回翻閱,發現簿上的字跡不盡相同,未看簡介,花點時間也能推敲出參觀者可在簿的左手邊留下一條問題,下位參加者回答以後再翻到下頁留下新的問題。你可能曾於問問題的人在灣仔區內相遇過,有過一面之緣卻又擦身而過,然後你又無法得知自己的問題在將來扣連上什麼,幻想空間無限,又浪漫又引人思考,回頭再看作品名稱,《連鎖對話》,噢,正是如此,不知創作這作品的藝術家劉曉江 Lawrence 為甚有這樣的構想呢?

2. 首次面談
Lawrence 個子很高,離遠已能在人群中看到他,我想起了一個壞笑話,就是說長得高的人看不見在他視線水平以下的人,可是 Lawrence 沒有不把人放在眼內,相反可能看得更貼地、更深刻。
Lawrence 的創作媒介極為廣泛,單是用「聲音藝術家」來介紹他實在說不過去。他的聲音作品包括室內樂、管弦樂、中國樂、現場電子樂、聲音設計、裝置等等,同時熱衷於在劇場創作中探索各種概念和語言。他上回在前奏展覽的作品印象中沒太多音樂元素,反而是錄像中被放大的環境聲與人聲絲絲細語交織,聲畫內容欲蓋彌彰,讓人忍不住更想專注聆聽觀察作品,想要找出其中線索。所以 Lawrence今次是想要作音樂以外的新嘗試?
Lawrence 從小就在灣仔居住,莊士敦道與軒尼詩道之間、修頓球場的四周就是他兒時生活、學習、玩耍、長大的場地。他對灣仔的認識與私密的回憶重疊,於街道間遊玩行走,上學回家的路上把人生百態盡收眼底。在灣仔中心,幢幢商住兩用大廈間上班居住的人們,沒有華美高級的背景,也沒有精彩起伏的大故事,但對本身就是灣仔一份子的 Lawrence 來說,草根的街坊每天在努力營役的場地,才是最真實的灣仔。
定義社區有很多種不同方法,客觀的諸如數據、測量、繪圖,然後再加以分類管理,但這真的能具體描繪社區的完整面貌嗎?Lawrence 想跳出地域性的硬定義,用雙腳、雙眼、雙耳,以聲音作為媒介,邀請灣仔人接受訪問,紀錄答案之餘,透過參與者的偶然發問和留下的一首歌曲,再與下一位灣仔人連結。作品或許能藉此建立起一個以日常對話來進行非日常的溝通的平台,讓被錯過的重新使人關注,讓從前平衡的從此交錯,結果且待 Lawrence 進行親身街訪才有分曉。

3. 街訪
街訪篇、黃雨日篇、漸秋意篇、攝影日篇…以上是 Lawrence 為每次走上街頭做的訪問命名,煞是浪漫,貫徹《連鎖對話》這作品的氛圍特色。我在其中一次街訪跟著 Lawrence和他的助手 Holmes,從修頓球場出發,沿軒尼詩道往金鐘方向,隨走隨訪路人。
可能我早以觀察員身份認識二人,有感 Lawrence 和 Holmes 皆混身散發著熱絡誠懇的氣場,正想這實在有利進行街訪,然而實情卻不是這樣。Lawrence 性格腼腆,要厚著面皮在路上攔截途人開展對話可說是人生一大突破,相反身為演員的 Holmes,有著劇場表演的經驗,憑對當代藝術創作的好奇和熱情,能幫上 Lawrence 一把,用親和力與陌生人打開話匣子。Lawrence 和 Holmes 以往一起在灣仔上班和工作,這助手不可多得,聖經說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的而且確我在路上看到了許多會心微笑的畫面。他們碰壁比成功的次數要多,眼看著他們細心觀察路上行人的不同狀態,推敲誰人較有機會駐足與他們交談,然後再乘勝追擊邀請,然而開口問十次有九次都被推卻,本著屢敗屢試的精神,我感動於他們的不氣餒、不放棄,回報就是遇上古道熱腸的灣仔人,慢慢把對話累積起來,成為下步創作的重要材料。
經過多次實戰經驗,Lawrence 有以下街訪心得:Less is more. 不作多餘的言語花飾,單刀直入就問對象想要留下什麼問題,然後方慢慢解釋計劃內容,通常會較易把受訪者留住;採訪地點也同樣關鍵,香港城市空間狹窄,商務繁重的灣仔尤其缺乏讓人站著停留的地方,所以盡量要找人流多但有位企的地方做訪問,譬如通往稅務大樓的橋上的人就比較容易留步交談,可能本身橋上經常有街站,經過此處的人們都有被人邀請談話的準備,對比地鐵站口和球場,會較容易找到街訪對象。最喜出望外是他們本以為下雨天難以進行街訪,卻想不到在黃色暴雨警告下避雨的途人反而更掏心對話,可能是大雨中同擔一把傘的化學作用吧。
Lawrence 形容街道本身就像河流,河流與河流之間既會交匯,亦會分流,在分別和相遇之間,藝術家正好遇上了受訪的陌生人,就像在河流相會的魚兒,不知擦身而過後下次再遇是何時,但是大家卻都在這藝術創作之中留下了交流的軌跡。我感覺Lawrence將自身對灣仔社區的感情都盡化成詩意的描繪,石屎森林再壓迫再喘不過氣來,只要有一剎找到固且信任的人短暫交談、分享一樣的地域回憶和感悟,舒一口悶氣,又或是互相拍膊頭打氣,那種排練不來的共鳴和暖心的溫度就是彌足珍貴。
我最記得藝術家不徐不疾走到灣仔循道衛理中心,門前是個鮮有人注視的接待處,他們思忖桌前的工作人員會否回答問題,還是鼓起勇氣走上前,對方可能因久坐在街上也很少人上前查問,遇到兩個年輕人提問也有仔細思考,認真回答,在這個在宗教場地前的對談顯得份外和善美好。問 Lawrence 最印象深刻的對談為何?他不下一次提起那個與他們詳談數個小時的球場婆婆。他記得一開始那個婆婆其實沒有很想回答提答,卻不住追問計劃內容,表示自己不明白時下年青人的想法,接著就是侃侃而談自己對這城市的感受和想法,Lawrence 並沒有因此抽身而去,卻非常有耐性地聆聽婆婆的話。他當下感覺,婆婆或許很少遇到會和她聊天的年青人,計劃好的一問一答在此刻已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原來有這麼的一個街坊的聲音是多麼地渴求被聽到。
情感勞動是 Lawrence 進行街訪的深切體會,在進行為期兩個多月,他成功採集了不少灣仔街坊的問題與答案,相等於與眾多互不相識但又長久生活在同一社區的人巧妙地連結起來。Lawrence 的創作不是街頭的商業問卷調查,在藝術家的設想中,這作品與受訪者的交往不會戛然而止,卻會在接下來的神秘音樂約會延續對話。

4. 神秘音樂約會
在赴約往《連鎖對話》的「神秘音樂約會」前,我到 Lawrence 的個人網頁上「溫習」了一下這數月來的街訪錄音,想像這些聲音的主人現身於這場音樂約會時,與那個不曾見面卻又已悄然交流過的陌生人相認的場面,實在令人充滿幻想和期待,並為大家已經熟悉不過的灣仔區帶來一點點驚喜。
音樂約會在位處大坑、活化後的虎豹別墅,現稱虎豹樂圃的戶外庭園舉行。進場時工作人員遞上耳機,以及寫有參加者在稍早時留下給下一位參加者的問題或歌曲名字的名牌,讓大家別在胸前,以作二人相認之用。這個 Silent Disco 以及眾裡尋他/她的活動設定立時替約會添加趣味。Lawrence 在不遠處的主控台前為參加者聲音導航,首先簡述大家相會在此的原因,以及作品的創作背景。他把街訪收集而來的歌曲及對話內容編成音樂約會播放的樂章,加上現場設置的聲音藝術裝置收集現場參加者的回響話語,即時再生成屬於當刻的聲景,全部聲音皆經由每人配戴著的耳筒廣播直達眾人耳蝸,有人手舞足蹈,有人閉目聆聽,時而走列咪高峰前回答 Lawrence 的提問,時而走到不同人的身旁打招呼,沒有配戴耳機的旁觀者一定會覺得畫面怪趣,卻不知道靜默的環境之中有一班人私密地分享著同一片大氣電波。
這場約會裡,有新知有舊雨,他們都告訴了我一些個人體驗。居住在跑馬地的 Daniel 是音樂愛好者,認識這個計劃的契機是來自 Lawrence 的音樂創作背景。 Daniel 從外國回流,比較少有參與灣仔社區活動的經驗。說到社區參與,對比起以往停留在社區中心做義工等刻板印象,他有感近年各區都多了文藝創作介入的社區活動,對年輕一輩來說吸引力大增,鼓勵他多留意區內舉辦社區藝術活動的消息,加上想多認識區住的社區的文化和歷史,甚至希望能結識更多有相同志趣的鄰里,所以就主動參唔這次約會,意想不同形式新潮有趣,一改他對參與社區事務必然正經八百的認知。他十分喜愛 Lawrence 的歌曲改編,認為 Lawrence 用才華巧妙地將從不同年齡層搜集而來,橫跨數十載、不同語言的歌曲編輯成動聽又不落俗套的輕巧舞曲,效果出色,他亦不其然與現場其他新相識的街坊一起跳舞,渡過了一個愉快的社區週末。
現場有一位街坊格外醒目,74歲的May姐原是灣仔利東街重建前的街坊,多年來關注區內重建發展進程,當初接觸過社區藝術這創作媒介後感覺新穎,不住參與相類近的項目,想要見識更多和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May 姐在幾歲跟家人參觀過虎豹別墅,有感孩提時未懂欣賞建築之美,到有能力自己遊玩時虎豹別墅已不復當年面貌,「弄丟了的鑽石是最大顆」,所以把握是次機會程訪一別數十載的景地。她坦言絕少參加音樂派對,自己不是音樂人亦不懂音樂,但當耳機偶然傳來她認識的時代曲的旋律,馬上就能代入其中,身體跟著拍子郁動,想到同一天空下有人跟她一樣認識點唱認識的歌曲就感到有種無形的連結,偶有時空暫時停頓之感,又想到物是人非,個人感嘆一言難盡。儘管沒有狂歡跳舞,但在口罩之下有不少不相識的參加者跟她點頭微笑,也非常滿足,在視覺和聽覺上有嶄新體驗之餘,也得到一份溫暖。她希望日後可參與到更年青藝術家的社區創作,希望藉此認識不同年紀的人所帶來的不同城市面貌,享受藝術創作的虛幻切入現實所帶來的無區無束。
我心口別著的名牌是「對你嚟講呢兩年灣仔最大的變化是什麼?」不用和在場新識的街坊朋友傾談都會知道,不同問題對大家來說都一定有不同答案。這些答案因人的私密經驗各異而不盡相同,又因各人共用同處灣仔這一地方而共享公共性,有地域重疊的部份,和而不同,兼容並處。活動巧妙之處是問題的答案是開放式的,甚至乎可以用《連鎖對話》中各位街坊分享的曲目作答。活動當日參加者與參加者之間的交流頻繁,我想是因為氣氛使然,人們聽著滿有內容的聲音作品,想獨處的可細心拆解聲帶的組合或是單純地欣賞音樂,想跳舞可自己原地舞動或是走入躍動的人群之中,想了解多點活動前因後果又可到台前閱讀藝術家的筆記和前奏展覽的留言簿,想認識新朋友又有問答環節或是留聲裝置去作免去尷尬的破冰,現場熱絡但又沒有群體壓力,緊密往來但又沒侵犯私人空間,令人感覺自在。社區的縮影不過如此,即有團體又有個體,每人都有一席位置,互相尊重,互相欣賞,沒有誰比誰微細,也沒有誰比誰重要,在如此容讓的藝術創作之中,我好像看到了平等,以及計算不來的真誠連結。
天色漸黑,參加者各自離去,我注意到現場還有兩位女生仍在談話,似乎沒有注意到人影開始零落,她們完全沒有離去的意思。初時以為二人是結伴同行的朋友,可是到後來她們又姿態客氣地道別,分頭離開。我立時上前詢問其中一位女生小星,她的參與體驗是我認為在整個觀察旅程中最戲劇性又最為美麗的故事。她的參與始於前奏展覽,她在參觀時有在便條紙上留下了一首歌,往後就沒特別在意紙條傳了給何人,直至收到計劃的活動邀請,勾起了延續參與社區藝術的興趣,以及與接下她歌曲紙條的人碰面的好奇心,她就到 Lawrence 的網站複習了街訪紀錄,然後來到約會現場,好好感受這個獨特的灣仔週末。
差不多待到散場都沒有遇到那個與她發生「連鎖對話」的人,小星準備抽身離去之際,就有一個女生上前,拿著有小星字跡的紙條說「你好」,二人就展開了對話。那個女孩首先道歉,說自己遲到,怕找不到留下紙條的人,失去了第一次,亦可能是最後一次和寫紙條的人相遇的機會。在7月得到紙條後,到12月的這個約會,整整五個月,她都珍而重之地把小星的紙條收藏在貼身的錢包裡,上面恰巧寫有一首她認為很重要,但又無法唱出的歌。她無法貿然向陌生人展示紙條,不知道何時可再展示紙條,偶爾在灰心無力時看看紙條鼓勵自己,告訴自己在這城市一隅,還有人與她一樣,然後默默地把紙條收回銀包,帶它到處去。直至此時此刻,她終於可以再次把紙條拿出來,告訴那個留言者,你的歌,也是我的歌。小星形容相認的感覺微妙,好像在和陌生人交換最心底的秘密,將不能宣之於口的私密事憑歌寄意,兜一大個圈找到了不相識的同伴,親身相見,聽女孩訴說感受時,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因為這是實實在在的連結,在低氣壓的大環境下實是令人心頭一暖,而且那溫暖會延存。她們當日只交換了感想,共識不交換聯絡方法,重疊的軌跡點到即止,讓相遇停留在記憶,和錢包之中。
除了神秘音樂約會的聲音作品外,如果大家想了解 Lawrence 的創作成果,還可到他的網站上聽聽街坊的問題和答案,Lawrence 並把在展覽和街訪結果搜集回來的歌曲以年份分類,整理每首歌曲出現的次數,製作成兩張屬於灣仔街坊的度身訂造歌單。參與計劃的街坊下意識想要與別人分享的曲目,在此化成一幀獨特的灣仔音樂地景,錯過了神秘音樂眾會的人,也可為舉行一場屬於自己的連鎖對話。
觀察紀錄 #4-1
聽見自己的故事
張薇(計劃觀察員)
每次回想「約素黑相睇告解」,記憶都自動地將整個氛圍調整成一次在大樹下聽故事的經驗。我帶著自己的故事前來,過程中卻聽見了自己。與參加者不曾碰面,卻感覺似是和他們共享了一場空間體驗。在個人經歷漸漸失去講述平台的今天,很想重新尋回故事的身價。

觀察紀錄 #4-2
有故事的空間
張薇(計劃觀察員)
帶著由素黑愛自己心語導引出的故事,遊走城中多個「愛自己漂流點」,像是將自己一點一滴地稀釋在城巿空間中,自此在這個社區將看到不一樣的風景,每個街角、每片天空都有自己才讀得懂的暗號。

觀察紀錄 #4-3
城巿中的幽壑
張薇(計劃觀察員)
在迷霧中,山谷有多闊,你只能大叫一聲,然後從它的回音來判斷。界限為你描劃了空間,紛擾讓你辨認出寧靜。問題是,我們常常看不到界限,習慣了紛擾。素黑的「靜靜地打開五感」原來不是給你靜,而是讓打開感官,懂得感受自己,才知道是否找對方向。

觀察紀錄 #4-4
都巿幽壑——素黑的空間營造
張薇(計劃觀察員)
《見山不是山》跨領域藝術計劃是在灣仔區舉行的社區藝術活動,其中一位參與藝術家是治療師兼作家素黑,她的活動「和自己相認體驗」分三部分:「約素黑相睇告解」、「愛自己漂流卡」和「靜靜地打開五感」。每一個環節表面看起來都很個人、私密,指向內心,但當整個活動框架放在社區的場景中實行,效果除了是透過她老練的治療技巧,讓參與者的內心得到體悟,她亦帶領參與者,透過個體意識的提升和故事的力量,參與了一個空間構築的過程。
心靈的榕樹頭
第一個活動「約素黑相睇告解」,這是一對一的會面,開放予社區人士報名。會面地點之一是灣仔藍屋幽靜內庭的一角。大樹下的一家樸素小館,這天只作與素黑約會的空間。由於內容極度私密,旁人無從觀察,甚至與其他參加者打了照面也會擔心不小心窺視了別人內心還未關好的門窗。
想了解過程就只能交出自己,成為一個「告解者」。每一個走進來的人,都先要從散佈在枱面上每一張都不一樣的「愛自己漂流卡」,隨機抽取了一張。素黑由這張小卡上的「愛自己」話語開始,導引出來者的內心故事⋯⋯說是來「告解」、吐心事,不過,有趣的是,從這個空間走出來後,發覺更像是前來聽了一場故事。
這應該就是素黑希望來者做到「愛自己」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在運作——好好的聆聽自己。我「約素黑相睇告解」的經驗,就像是參加了一場心靈的榕樹頭故事會。我帶著自己的故事前來,而素黑像是一個具魔法的「說故事的人」,閱讀著我的經歷,並以她作為一個治療師獨特而敏銳的溝通方式,導引我反觀自身,以素黑自己的話,就是「#你不是來看我你是來看你自己」,最終的效果,是讓我獲得一個聆聽自己故事的體驗。
在「約素黑相睇告解」整個過程,素黑共在6天與生活在灣仔這個社區的人(這是活動報名條件之一)會見,這群人帶著他們零碎、尚未名狀的情緒,來到這個心靈的榕樹頭,讓素黑設定的「愛自己」主題給予故事一個輪廓,一個說出來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一個說出來的理由。這些故事,在這裡被釋放出,活動過後再跟隨故事主人回到故事生活的社區場景繼續演化。
每個人內心的幽壑都是其他人無法到達的,除了自己,無人可以「在場」。治療師的獨特身份,讓一個人願意邀請她進內(雖然也許有時只是打開一小片門縫)作短暫探訪。一直以來,同時是作家的素黑都在著作中,將她接觸到的無數個案,隱去真實身份後,書寫出來,讓這些個人的、隱閉的內心風景,得以被記錄、述說。
素黑說過,她寫的不是「故事」而是「經歷」。她想強調的是她的書寫,是源自真實的「經歷」,而非虛構的「故事」。其實,她對待每個收集回來的「經歷」的態度,更像是要回歸班雅明所說的「故事」最原初的特質。
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一文中提醒我們,在人與人的溝通仍以「口口相傳」形式進行的年代,「故事」的身價就來自它源於「經驗」——「說故事的人的材料,如果不是他本人的經驗,便是傳遞而來的經驗」。在過去,「說故事的人」(或者叫做「敘述者」)的兩種典型,是遠遊歸來者(以「水手—商人」為代表)和定居者(以農民為代表),他們的共通之處都是擁有豐富的閱歷。人們透過在榕樹頭或廣場聚集,聆聽這個見多識廣的人講述他的種種見聞,來建構起對世界的想像。
班雅明亦指出,故事「或公開地,或秘密地具有實用功效。這個實用功效有時會以一句格言或是一條行為法則來轉譯,有時會轉譯成一個實用的建議,有時候則是一條道德教訓;無論如何,說故事的人,對他的聽眾來說,乃是一名良好的顧問。」
在「約素黑相睇告解」,她以一句「愛自己」的忠告語切入,啟動參與者的高度自覺狀態,一小時的面談經驗,讓分享者聆聽到自己——一場有著自己作為敘述者的獨特語氣的故事,的確是一趟奇秘的體驗。

漂流的故事
素黑充滿自愛能量的心語,結合三三繪畫和書法的自在從容,成為一套二十張貼心的「愛自己漂流卡」,放在灣仔區的六個地點,讓人隨意抽取,與自己喃喃細語一番,然後在下一次到訪或在下一個擺放地點,交換另一張。你可以讓自己的心情在不同的小卡間漂流,或是帶上小卡,連同自己的心事, 從城巿的一點漂流到另一點。
「愛自己漂流卡」上的心語,是素黑多年來在療癒工作與無數人的經歷相遇而累積的智慧,或者就如班雅明所說的,每個說故事的人都會向他的聽眾提供具實用功效的格言。這是說故事的人從實際生活體驗中提煉而來的,能為聽眾所經歷的事情朝什麼方向發展下去給予建議。
十一月的某一天,在繁重的工作中出發去探訪我的第一個漂流點,位於天后歌頓道的oneironaut夢旅人Café,我抽到的漂流卡寫著:
「這些日子不容易
知道你累了
沒事的,
你不是一個人」
我點了一杯咖啡,想著自己這段日子的經歷,也想像著這張卡的前一個主人的故事,然後,我帶著這張卡和卡上承載的所有故事,坐上西行的電車,來到第二站是銅鑼灣霎西街的窗後巷,我放下這張卡,換上另一張:
「你有你的尊貴
你不是來陪襯
世界或別人的」
這正是我在較早前參與「約素黑相睇告解」時抽到的那一張。兩段經歷接駁起來了,在當中這張愛自己漂流卡的確為如何繼續前行提示了一個方向。這種靈犀,並非偶然,它就是反映了這種來自故事的格言的務實功用。我帶著這張卡,出發前往下一個漂流點。
只要親身踏足過這些地點,就不難發現這些精心挑選的小店/空間(SP Dance and Gift Concept、Jack's Flowers、香港故事館、夢旅人Cafe、SINCE Concept Store、窗後巷),本身都藏著滿滿的故事,並且都具備某種感性的氛圍,自然地與你的故事交織滲透。
素黑挑選的這六個漂流點,散落在天后至灣仔之間,帶著小卡一一探訪不同漂流點的經驗,是一個將地圖上的點與線,開展為真正的城巿空間的體驗,並且因你特定的遊走目的和方式,為這個空間賦予獨特的意義。
空間理論學家de Certeau提醒我們,每一個故事都是一個旅程,每一趟行走的經驗都是一個空間的實踐,而一個空間的真正意義是由人的使用產生的。帶著高度自覺的個體意識使用空間便是最有力的空間營造,而且愈個人化,這個空間的意義就愈難被他人的定義所取代。

內心的幽壑
素黑設計的第三個活動是「靜靜地打開五感」,是一場透過音叉、銅磬、框鼓和茶修等打開五感的體驗。她聯同樂師Ocean、茶師李天安,一起在喧鬧的灣仔,讓我們體驗了不同程度的意識提升。
參加者透過愛自己漂流卡上的心語,啟動對自我的自覺,接受不同音頻對五感的刺激。
聲音和味道,可以將空間的領域感,以可感知的方式傳遞給在場的參與者。音波的迴盪振動,帶給我們對空間界限的感知。原來,習慣了紛擾,會令人失去辨認平靜的能力。這晚的打開五感體驗,原來不是為你帶來平靜,而是讓你感知你有多不平靜。看到了限界,才想像得到遼濶。
這晚,我的內心出現了一座幽壑,餘音飄渺。

觀察紀錄 #5
灣仔大夢
黃嘉瀛(計劃觀察員)
1. 前奏展覽
小時候看國際奇趣新聞有很多怪異又讓人印象深刻的奇聞,其中一個是在外國,有人發現了一種睡眠障礙病叫「快速動眼期睡眠剝奪」,患病的人在入睡之後不會進入快速動眼期,所以患者不會作夢。不會作夢的病人在白天會兩眼無神,人們講話則有聽沒懂,短期記憶還可以,但沒辦法透過睡眠作夢來形成長期記憶。原來不發夢也是一種夢……我在想,這個城市可能已經有好多人被逼患病,難怪好多在馬路兩邊等綠燈的人雙眼失焦,彷彿在告訴大家,我們不能、不可以發夢。可是應該有更多的人一直堅持做夢吧。
有人說,做藝術就是在做夢,那麼夏天在集成中心舉行的前奏展覽大概就是無夢的都市中,意外地允許人大膽做夢的綠洲吧。我在展覽入口不遠處,就望到一度原木的大門,大門有拒絕進入的意思,也可以是被批准進入別人私密場域的邀請。走到展品面前,就知道這是一個邀請。門前放著三張大小和樣子不一的椅子,有一張是全黑色的流線型現成椅,上面帶有使用痕跡,另一張是殖民時代常見公務木藤椅,當然也有一定的年代感,兩張椅中間放了張圓木摺凳,就是最地道大排檔用的那款,那幾乎可以說是香港名物。乍看這些椅子羅列起來,根本就是平日在路旁、在巴士站、在士多前的「社區椅子」模樣,將不要的或是多出來但仍可以坐的椅子放到公眾地方,讓有需要的鄰里享用,三兩個街坊圍坐在一起或乘涼,或聊天,本身就有開放加入和邀請的意味,任誰路過都可隨便使用,不會有被排拒的感受。
這或許就是藝術家吳暐君 (Sharon) 的作品《灣仔大夢》的本質。摺凳上面放有一些Sharon親自設計的邀請卡,上面寫著「你有冇夢境係發生喺灣仔?」如果答案是「有」就接續詢問夢境是發生在灣仔哪處?夢中發生了什麼事?你夢中的情緒又如何?……這一連串的問題實在是引起人莫大的好奇心,對「夢」稍有感覺的人也會忍不住細心回想自己發過的夢,希望能找到些許與「灣仔大夢」連結起來的線索。如果有些眉目,你可坐在椅子上,拿起鉛筆,在邀請卡上寫上答案,在前方的木門上有一投信用的空隙,把填了你那私密的、關於灣仔的夢境留言投往門後。我很好奇有多少人回覆,有多少人曾在灣仔發過大夢?繼續想像下去,就像電影電玩的情節那樣,原來夢境也可共享,我們或許在同一個夢境中的那同一個灣仔相遇……
實情卻可能沒那麼浪漫。門上還有一張海報,海報分兩邊,一邊是Sharon設計的灣仔輪廓地圖,寫著「我嘅夢境發生喺……」,一邊就是問題和空白位,寫著「我無夢境發生喺灣仔。」參觀人的人可按Sharon設計的問題,用紅色小點貼紙標示自己的答案。現實往往是毫不詩意的,按海報上的貼紙統計顯示,沒有做過灣仔大夢的人似乎比發過灣仔夢的人多。但是在地圖上邊密麻麻的紅點,又在說明發過灣仔夢的人確實記得那些夢的內容,甚至指出了明確的地點,更加令人好奇他們的灣仔大夢是什麼樣的呢……
這次Sharon為灣仔度身訂造「灣仔大夢圖」,社區不只作為人們現實生活的場域,亦是市民發夢的主舞台。她由七月開始在灣仔街頭擺設「捕夢站」,並設立了「夢境話語」留言信箱及線上「捕夢站」,去收集市民曾做過關於灣仔的夢。在搜集夢境以後,她進一步連繫這些夢的主人,以工作坊和聚會去深入探索這些夢境和發生地點的意涵和故事,將似有還無的片段、抽象的情緒、遠去的記憶,確切地與灣仔再次連結起來。
我非常期待在接下來的工作坊,可以聽到那些未為人知的、發生在灣仔的夢境故事,以及親身認識這些夢境的主人呢!



觀察紀錄 #6
永遠平行的社區,寫在迎難而上之後
阿三(計劃觀察員)
一、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區,藝術從來都在你我生活之中。聽起來似是「阿媽係女人」的廢話,認真點去想,其實跟「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只是山」(註1) 禪宗一席話異曲同工。
「社區」(community)一詞強調「整體」或「集體」(asawhole),不論因為居住地理環境、信奉宗教、從事行業,或屬某一種族;同時,它亦指人們共同擁有或享有一些東西,可以是實質的空間、物件、財富,或無形的價值觀念及習俗等。至於藝術,不必來個美學申述或思辯。這裡說的是廣義的文化藝術,不是牛頭角順嫂口裡「我唔識藝術」的高雅形式。另一邊廂,不同藝術形式發展成固定又獨特的模樣後,人們要去學習唱歌或跳舞,認識舞台語言或演戲技巧,練習寫生方法或駕馭物料應用,才能擠身藝術的舞台。後來,現當代視覺藝術圈有人出來說「人人都是藝術家」或「藝術應該屬於所有人」,並身體力行以創作體現觀念。我們現在討論的「社區藝術」的理念與實踐方法,便慢慢成形。那我們得細想一下,藝術本在社區的前提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不是高高在上的專家。他們應該扮演甚麼角色,秉持甚麼原則實踐,才不會出現「藝術(家)需要社區多於社區需要藝術(家)」本末倒置的尷尬情況?
「社區藝術」(communityart)是人們發明的概念,其核心在於「文化民主」(culturaldemocracy)。這是指文化及其詮釋權並非掌握於某些人手中,各持份者(stakeholder)享有平等權利。社區藝術人人可以參與,執行者應該致力降低或消除門檻;同時,讓最多的人知道自己有權參與,不關乎「藝術天份」與能力,卻在於啟動其參與意欲及熱忱。牛頭角順嫂或廟街阿叔有權說出自己想要的文化生活,豬肉佬夢想成舞蹈家並不可笑,社區藝術計劃該成為綻放多元聲音的場域。此外,人們在社區藝術裡須建立具意義的長期連繫,方能令本就在社區的藝術茁壯成長。藝術家或擁有相關藝術理念的策劃者的角色是透過具創意的方法,豐富既有社區關係,構建陌生人的連結,及發現未知或未被看見的人際網絡和社區意義。換句話說,我們對社區藝術的想像,應該不限到社區教跳舞,跟街坊排一齣劇,或一起畫一張壁畫,完成了計劃便悄然退場。

二、
「十八有藝——社區演藝計劃」(註2) 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社區節目辦事處計劃。2021-22年度各區項目演藝類型包括音樂演奏、歌唱表演、音樂劇、劇場、街舞、粵劇及劇偶表演,其內容有培訓、示範、工作坊、講故事、攝影及文學地景等。社區節目辦事處「負責策劃兩大類別的節目,即全港節慶活動和嘉年華會,以及在全港舉辦的地區文化藝術節目」(註3)。節慶,是地區文化的重要部份,世界各地不少著名文化節目,均與當地節慶有關。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將「節慶」(festival)、嘉年華(carnival)與「社區藝術」(註4) 扣連起來並非必然,實踐社區藝術也不一定透過「項目」(event)。(註5) 如果「節慶」的想像等同「社區藝術」的想像,並以「項目化」執行,可會收窄後者的範圍、可能及生命力。
香港民間主導的社區藝術計劃多不勝數,各自各精彩。其盛放原因是否因為近十多年來公民覺醒及公民社會重新建立,或本地經濟轉型後都市仕紳化及財富不均,令不少市民轉投文化事工,有待相關學者及專家深入研究。輕輕數一數有關社區藝術的民間團體,有灣仔藍屋及香港故事館(組織及空間)、活化廳(組織及空間)、社群藝術網絡(組織)、C&G藝術單位(藝術家組合)、藝術到家(組織)及「天拉吧」天水圍故事館(組織及空間),他們均累積了一定的成果。他們也曾籌辦過節慶及嘉年華,可佻皮活潑地重新定義兩者意思,改頭換面跟街坊共同過一個別開生面的「節慶」。
「見山不是山」(註6) 為「十八有藝」灣仔區項目,由No Discipline Limited策劃。No Discipline Limited在此計劃中十分強調藝術經驗,「社區藝術不必然只在於功能、服務或解決問題等單一模式,社區藝術也可以開闊感官和經歷,發現『境』可以隨心轉,原來環境、甚至自己,可以如此寬廣、可以如此不一樣。」(註7) 可是,落入「十八有藝」的「演藝」框架,一對一的「約素黑相睇告解」或到公園一起掃落葉算不算是「演藝」活動?No Discipline Limited有意識地叩問各類既定藝術形式的邊界,及它們可有重疊或重新劃定的空間?「耳蝸裡有隻象」(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2021)相對較貼近劇場,舞台設計及與觀眾關係卻根本是個環境裝置。「見山不是山」其中一位策劃人黎蘊賢的「火花!像是動物園」(油街實現,2014),多傾向視覺藝術的展覽形式,又加入演員帶領的另類導賞與即興劇場體驗。社區,不是能給我們預想的對象,更不是對號入座式埋位等派禮物的活動。面對雜亂紛陳的生活,我們對人——構成社區的重要元素——的認知顯得相當有限。所以,主導及策劃項目者該更開闊胸襟,發現不同社區獨特個性,成就每位持份者的期望。
理想歸理想,現實還現實。「十八有藝」計劃方向與「見山不是山」概念觀點存有落差,積極來說本應能擦出火花,為「節慶」和「嘉年華」以外尋找更多可行方案。然而,不正常的疫後新常態秩序下,若干藝術家原初想法無法圓滿落實,「驚濤駭浪」下總算完成,而黃進曦的寫生活動更無奈地取消。是次經驗,不得不叫我們反思官方與民間對社區藝術想像的落差;及於嚴謹防疫限制下人與人被阻隔的現況,社區環境扭曲或萎縮,可以怎樣重回生機?

三、
「見山不是山」幾位觀察員參與、觀察、訪談及回應各項目的文章,已清楚寫出藝術概念及項目值得討論的地方,本文不必重複。不過,這裡想補充一下五位藝術家執行方法的一些共同特點,及相關隨想。
社區藝術其中一個主要部份,是邀請人們分享自己的看法與感受。人們一向可以在榕樹頭下或公園仔旁一述己見,那麼藝術介入用意何在?素黑、吳暐君(Sharon)及劉曉江(Lawrence)對分享的想法各有不同。素黑是心性療癒師,她安排的一對一「分享」是種信念式告解,參與者釋放個人經驗與療癒師如何引導及回應,旁人無從得知。正因她這個專業身份,令到「聆聽自己」及「愛自己」變成往前的力量。Sharon的街站捕夢工作,可以跟素黑的有一丁點相似,如果報夢人的夢跟其潛意識與內在自我有關。夢,可以很個人,是近日生活的投射或人們根本性情的一面鏡;它也可以解作寄願,是渴求未達至的東西,或不能張口的慾望與禁忌。而後來在伊利沙白體育館舉行的工作坊,觀察員戲說似是聚集陌生人的秘密宗教活動。誠言,Faith可解作宗教有關的「信仰」或支撐生存之道的「信念」。在亂世逆流下,人們的確需要這種Faith。說到連結陌生人,Lawrence仿如街頭問卷調查員,收集路人的提問;再變身傳訊員,將問題帶給下一位陌生者。藝術家均有意識及組織地以原社區不存在或不被看見的方式,把各人心中相近的看法與感受放置於同一平台上。
社區藝術也關乎空間,包括空間屬於誰,及我們可以在那裡做些甚麼。程展緯(Luke)的項目除了思考「公共」和「大家」的概念,亦強調人們在社區有其義務。在公園裡放置掃把讓街坊隨時來打掃落葉,猶如落雪地區居民一起剷雪的集體生活,卻不是各家自掃門前雪,更不是聘請管理公司再外判清潔工來定期解決衛生問題。Luke這提議簡單不過,惟我們似乎忘記了最原初的責任,和社區關係。許敖山(Steve)街頭唱歌最初想法,其實跟在榕樹頭分享一下街市行情或全家不幸感染肺炎經驗一樣,不必勞師動眾,也不一定如Busker一樣搬動專業音響器材。有人就能發聲,多幾個人便能合唱,街頭任何一處都是舞台。Steve選的粵謳的確與街唱或社區無關,而跟廣東話多點意思;Lawrence籌辦的「連鎖對話約會」,所選的廣東流行歌,跟Steve的粵謳意義不言而喻。語言是文化身份,也是我們與地方的其中一種直接歸屬。素黑「愛自己漂流卡」放在灣仔區六個地點,邀請人們走訪灣仔,體驗社區。同時,這浪漫的做法令人想到圖書館書本曾被人寫下的筆記或夾下的字條,及電影《情書》裡偷偷寫在借書卡的字。公用的東西便有人的溫度,不限是掃把、書本或一張卡,也釋放關於社區的一些話語。語言結構建基於約定俗成的規則,及解讀語境。把任意抽取或遇上的字句逐一拼起來,本就是現當代解放語言邏輯的作家曾嘗試的創作方法,他們尋求的是文學的意義。字句不止於它寫下的內容,也在於閱讀者的領悟與詮釋,及當下香港的社會氛圍。正如,同一首歌曲置身於不同的年代,進入不同的人耳蝸,泛起的感情會截然不同。
社區並無固定形象,社區藝術亦無終極方向。要把「阿媽係女人」藝術原則或策劃方法一二三變得有意義,不是光靠藝術家的外力,而是靠大家,社區裡的每一位持份者。大家在工作與私人生活之外,可曾有些微空間想想身處的社區,感受及發現它的特質,再問問自己可以為這個地方做些甚麼?社區藝術不一定要靠資助撥款(儘管這樣好似倒文化人的米),改變現況也不一定需要Marvel或DC漫畫裡身懷異能的英雄。社區尚在,未來怎也會來臨;還在香港社區裡的我們,共勉。

註1:「見山不是山」計劃名稱,取自禪宗《五燈會元》。該書籍記載唐代禪宗大師青原惟信的一段話:「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即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
註2:各區計劃詳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十八有藝——社區演藝計劃」網頁:https://www.lcsd.gov.hk/tc/cpo/18dart.html,2022年3月30日瀏覽。
註3:英文演繹為「The Community Programmes Office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organising two main categories of cultural programmes, i.e. territory-wide festive events and carnivals, as well as community cultural arts events held in Hong Kong.」。見於「關於社區節目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tc/cpo/aboutus.html,2022年3月30日瀏覽。
註4:「社區文化」及「社區藝術」於社區節目辦事處申述下幾近等同,其中一個目標為「在社區推廣藝術發展」。見於「關於社區節目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tc/cpo/aboutus.html,2022年3月30日瀏覽。
註5:香港各區社區文化活動節慶化的特性,有待進一步翻查。暫此可參考《彼此彼此——社群╱社區藝術訪談記事(年表及附錄)》第2頁的描述:「自七十年代的公共及文化建設、新市鎮等陸續落成,地區政策逐步(有限度地)民主化。各區除了鄉親節慶或公民教育類的宣傳活動外,均開始增辦各式區節、匯演、嘉年華。另一方面,七十年代社會運動、社區組織在居民和社群中結集力量,至八十年代中藉選舉走進建制,但運動中亦有部份開始關注自身及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文化權,甚至以文化行動介入社會。」。湯映彤、陳秉鳳及葉浩麟編:《彼此彼此——社群╱社區藝術訪談記事》及《年表及附錄》。香港:社群藝術網絡,2018年。
註6:計劃包括六個部份,即程展緯「大家的掃把」、許敖山「解心樂園灣仔遊」、劉曉江「連鎖對話」、吳暐君「灣仔大夢」、素黑「和自己相認體驗」,及黃進曦「凝聚視角」。
註7:見No Discipline Limited「見山不是山」版面,http://nodisciplinelimited.hk/index.php/portfolio/mountain-no-mountain/,2022年3月30日瀏覽。